国内大循环强起来
国内大循环强起来
国内大循环强起来潮新闻(xīnwén)客户端 梁新阳
 公元1942年(nián),农历壬午(马)年。
这(zhè)一年(nián),在不少新昌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(shēnchù),潜藏着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场景(chǎngjǐng)。据史料记载,1942年5月中旬,日本侵略军70师团8个(gè)步兵大队及配属部队8000余人(yúrén)从奉化入境分三路窜犯新昌,其中一路由儒岙进入回山,途经彩淳乡(今属回山镇)的上宅、下宅、下塘等村前往东阳尖山方向。日本兵烧杀抢掠,奸淫妇女,无恶不作,沿途百姓遭受无妄之灾。
父亲是个读书人(dúshūrén),1934年11月出生于彩淳乡下塘村,1950年代就读于新昌南明中学和天台简师,后在临海桃渚和新昌八和、彩淳等地小学教书。父亲为人沉稳朴实,平时也乐于做些济贫帮困的(de)善事,但对老家回山(huíshān)遭受日军侵犯,特别(tèbié)是爷爷被抓去做挑夫的那段往事,总是三缄其口(sānjiānqíkǒu),不愿提及。这也许是深藏在他心中隐秘处,一个(yígè)不想被激活的疼痛点吧。
母亲的(de)娘家在原彩淳乡上宅村西塘岙,山岙里只住着外公一户人家,从上宅村迁来。此地虽(suī)偏僻冷清,但不缺水源和(hé)山地,适宜居住耕作。外公不仅勤于农事,还在家宅后面的山上搭建了口土砖窑,农闲时便(biàn)雇几个帮工到窑场(yáochǎng)烧砖烧瓦,因而在当地也算得上温饱有余的小康之家。
母亲出生于1937年9月,正是那年的(de)7月,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,战争的硝烟弥漫到全国各地(gèdì),中华民族进入全面(quánmiàn)抗战阶段(jiēduàn)。母亲没上过几天学堂,少儿时看牛割草,稍大便参与农活劳作,识得的几个字还是村夜校扫盲班的功劳。与父亲沉稳少言的性格相反(xiāngfǎn),母亲热情开朗,今年已年近九旬,讲起事儿来还是知无不言,头头是道。
母亲说,那年(1942年)日本人祸害回山(huíshān)老百姓,是从石蟹岭爬上来的(de)。当时,外公听闻日本兵来了,就带着(zhe)家里的男丁躲避到远处的深山里,裹着小脚的外婆(wàipó)就带着她躲在(zài)离家不远(bùyuǎn)一个叫(jiào)前山的地方。那里是个乱坟堆,躲藏于此的原因,一来坟墓边上的树木参天,遮天(zhētiān)敝日,四周灌木丛生,常年碧绿,不近看难以被发现;再则逃难时走得急,又没经验,值点(diǎn)钱的东西都没有带在身边,不放心家里无人照看,所以不敢走远,躲在附近也算一举两得。不料,她们的藏身点与日本兵经过的道路隔沟相望,甚至可以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马嘶声。那时母亲自然是小心翼翼蹲坐着不敢有所声息,外婆却胆大心细(dǎndàxīnxì),从树蓬中(zhōng)找间隙望了望行进中的日本兵。事后,外婆还告诉母亲,那伙东洋人矮矮的,马是高高大大的。
那天,对母亲她们来说只是虚惊一场,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,距西塘(xītáng)岙不到一里地的(de)下塘村就遭了殃。
下塘村属于原彩淳乡,村落三面环山,南朝水口,村中民宅多在(zài)西北面高坡上依山而建。村口(cūnkǒu)建有一座水口庙,旁有一个古树群,形成一道天然的(de)(de)屏障,构成了(le)民间津津乐道的聚宝盆格局。村名古称厦堂,寄托着先人(xiānrén)的某种期望,早在元代就有人在此生活,后人为便于书写俗化成今名。明朝永乐十五年(1417)出了位才子杨宗器,名列会试副榜,官至山东郯城县知县。这个不满百户人家(rénjiā)的小山村,村民姓氏以梁、杨、王为主,历来民风(mínfēng)淳朴,耕读传家,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况。但在1942年5月,却没能逃过那场建村以来遭受的最大劫难(jiénàn)。
今年6月的(de)(de)一天,翻阅父亲2004年编撰(biānzhuàn)的《彩烟梁氏永思祠小房天祥公派世系图》,从中掉出一张不大的纸头。一看,如获至宝。原来是父亲用圆珠笔写的,对日军1942年5月在回山犯下的恶行的愤恨控诉。字数(zìshù)虽不多(suībùduō),但笔迹(bǐjì)端庄有力,入木三分,表达上义愤填膺,气势如虹。也许,父亲告诉过我,有这么一份资料夹(zīliàojiā)在那里,只不过当时被我忽视了;也许,父亲知道我一定会(huì)翻看到这份资料,只不过需要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罢了。果然,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(shènglì)80周年的2025年,这张静静寓身于书中十数年,寻常普通却很不一般的纸头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。
公元1942年(nián),农历壬午(马)年。
这(zhè)一年(nián),在不少新昌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(shēnchù),潜藏着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场景(chǎngjǐng)。据史料记载,1942年5月中旬,日本侵略军70师团8个(gè)步兵大队及配属部队8000余人(yúrén)从奉化入境分三路窜犯新昌,其中一路由儒岙进入回山,途经彩淳乡(今属回山镇)的上宅、下宅、下塘等村前往东阳尖山方向。日本兵烧杀抢掠,奸淫妇女,无恶不作,沿途百姓遭受无妄之灾。
父亲是个读书人(dúshūrén),1934年11月出生于彩淳乡下塘村,1950年代就读于新昌南明中学和天台简师,后在临海桃渚和新昌八和、彩淳等地小学教书。父亲为人沉稳朴实,平时也乐于做些济贫帮困的(de)善事,但对老家回山(huíshān)遭受日军侵犯,特别(tèbié)是爷爷被抓去做挑夫的那段往事,总是三缄其口(sānjiānqíkǒu),不愿提及。这也许是深藏在他心中隐秘处,一个(yígè)不想被激活的疼痛点吧。
母亲的(de)娘家在原彩淳乡上宅村西塘岙,山岙里只住着外公一户人家,从上宅村迁来。此地虽(suī)偏僻冷清,但不缺水源和(hé)山地,适宜居住耕作。外公不仅勤于农事,还在家宅后面的山上搭建了口土砖窑,农闲时便(biàn)雇几个帮工到窑场(yáochǎng)烧砖烧瓦,因而在当地也算得上温饱有余的小康之家。
母亲出生于1937年9月,正是那年的(de)7月,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,战争的硝烟弥漫到全国各地(gèdì),中华民族进入全面(quánmiàn)抗战阶段(jiēduàn)。母亲没上过几天学堂,少儿时看牛割草,稍大便参与农活劳作,识得的几个字还是村夜校扫盲班的功劳。与父亲沉稳少言的性格相反(xiāngfǎn),母亲热情开朗,今年已年近九旬,讲起事儿来还是知无不言,头头是道。
母亲说,那年(1942年)日本人祸害回山(huíshān)老百姓,是从石蟹岭爬上来的(de)。当时,外公听闻日本兵来了,就带着(zhe)家里的男丁躲避到远处的深山里,裹着小脚的外婆(wàipó)就带着她躲在(zài)离家不远(bùyuǎn)一个叫(jiào)前山的地方。那里是个乱坟堆,躲藏于此的原因,一来坟墓边上的树木参天,遮天(zhētiān)敝日,四周灌木丛生,常年碧绿,不近看难以被发现;再则逃难时走得急,又没经验,值点(diǎn)钱的东西都没有带在身边,不放心家里无人照看,所以不敢走远,躲在附近也算一举两得。不料,她们的藏身点与日本兵经过的道路隔沟相望,甚至可以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马嘶声。那时母亲自然是小心翼翼蹲坐着不敢有所声息,外婆却胆大心细(dǎndàxīnxì),从树蓬中(zhōng)找间隙望了望行进中的日本兵。事后,外婆还告诉母亲,那伙东洋人矮矮的,马是高高大大的。
那天,对母亲她们来说只是虚惊一场,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,距西塘(xītáng)岙不到一里地的(de)下塘村就遭了殃。
下塘村属于原彩淳乡,村落三面环山,南朝水口,村中民宅多在(zài)西北面高坡上依山而建。村口(cūnkǒu)建有一座水口庙,旁有一个古树群,形成一道天然的(de)(de)屏障,构成了(le)民间津津乐道的聚宝盆格局。村名古称厦堂,寄托着先人(xiānrén)的某种期望,早在元代就有人在此生活,后人为便于书写俗化成今名。明朝永乐十五年(1417)出了位才子杨宗器,名列会试副榜,官至山东郯城县知县。这个不满百户人家(rénjiā)的小山村,村民姓氏以梁、杨、王为主,历来民风(mínfēng)淳朴,耕读传家,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况。但在1942年5月,却没能逃过那场建村以来遭受的最大劫难(jiénàn)。
今年6月的(de)(de)一天,翻阅父亲2004年编撰(biānzhuàn)的《彩烟梁氏永思祠小房天祥公派世系图》,从中掉出一张不大的纸头。一看,如获至宝。原来是父亲用圆珠笔写的,对日军1942年5月在回山犯下的恶行的愤恨控诉。字数(zìshù)虽不多(suībùduō),但笔迹(bǐjì)端庄有力,入木三分,表达上义愤填膺,气势如虹。也许,父亲告诉过我,有这么一份资料夹(zīliàojiā)在那里,只不过当时被我忽视了;也许,父亲知道我一定会(huì)翻看到这份资料,只不过需要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罢了。果然,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(shènglì)80周年的2025年,这张静静寓身于书中十数年,寻常普通却很不一般的纸头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。
 父亲作为当年事件的(de)亲历者,他的口述(kǒushù)资料是可以作为一件反映抗战的辅助史料来保存的。所以,父亲写的这段文字,我觉得无比珍贵,也(yě)就一字不漏地抄录于此:
1942年古历四月初六(chūliù),一股日寇去衢州路过彩淳(cǎichún)时烧毁了下宅村一些民房,枪杀了我村外逃在山林和(hé)田野里的两名村民(林照和荷花),枪伤两名村民,奸污几名妇女,还抓了四名村民为他(tā)(们)担挑抢劫来的财物。其中一名长者(王相钱)惨死在东阳尖山,没有回来。当日晚,日寇还把回山的白王殿烧毁掉。日寇如此(rúcǐ)残忍,我们中国(zhōngguó)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
原来(yuánlái),对父亲不愿讲述日军侵犯回山这件事儿,我还真有误解。或许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,不属于茶余饭后的(de)谈资;或许是感觉场合不适宜,不想轻易揭开血淋淋的伤疤让人难受;或许还有其他的考量(kǎoliáng),比如不愿反复叨扰已经去了(le)另一个世界的受害者……
不说,不代表忘却,而是在心中早已深深(shēnshēn)扎根。
不是么?壬午(1942)年四月(sìyuè)初六,这个记忆中难以磨灭的(de)(de)(de)日子,让父亲整整记了一辈子。下塘村里受害者的人数,以及惨遭杀害者的名字(míngzì),父亲始终一丝不苟地记着。回山白王殿被日本鬼子烧毁的具体时间,一些文中的表述语焉不详,而父亲记得清清楚楚,是在那天的晚上。这短短的一段文字(wénzì),字里行间充满着痛与恨,痛心同胞遭受的深重灾难,恨透了日本鬼子的丧尽天良!
爷爷应该是村子里被抓(zhuā)去当挑夫的(de)四个人之一,凭着正当壮年而又常年劳作(láozuò)的结实体魄,总算(zǒngsuàn)熬过一劫,历尽千难万险后逃了回来。至于那天爷爷带着家人一同外出躲藏,怎么会被捉去?当挑夫遭受了哪些地狱般的磨难?又如何逃脱成功?这些都成了解不开的谜团(mítuán)。数日前与母亲聊起此事,她只知道爷爷被迫当挑夫时,挑着重担走得慢点就(jiù)遭鬼子敲打,还经常忍饥挨饿,身体就这样弄垮了,回家后生了场大病(dàbìng)(bìng),落下难以治愈的病根子。最后母亲感叹:“天下勿太平,日子就难过。”
现在我很想与父聊聊,可他年事已高,说话含糊不清,数年前脑梗后一直在医院康复。我去康复病房探望父亲时,专门告诉他,祖国强大了,外敌(wàidí)入侵(rùqīn)已成历史(lìshǐ);但遭受外敌侵略的历史,我们永不忘记!父亲肯定听明白了,他的眼眸陡然间闪过一道亮光(liàngguāng)。
父亲作为当年事件的(de)亲历者,他的口述(kǒushù)资料是可以作为一件反映抗战的辅助史料来保存的。所以,父亲写的这段文字,我觉得无比珍贵,也(yě)就一字不漏地抄录于此:
1942年古历四月初六(chūliù),一股日寇去衢州路过彩淳(cǎichún)时烧毁了下宅村一些民房,枪杀了我村外逃在山林和(hé)田野里的两名村民(林照和荷花),枪伤两名村民,奸污几名妇女,还抓了四名村民为他(tā)(们)担挑抢劫来的财物。其中一名长者(王相钱)惨死在东阳尖山,没有回来。当日晚,日寇还把回山的白王殿烧毁掉。日寇如此(rúcǐ)残忍,我们中国(zhōngguó)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
原来(yuánlái),对父亲不愿讲述日军侵犯回山这件事儿,我还真有误解。或许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,不属于茶余饭后的(de)谈资;或许是感觉场合不适宜,不想轻易揭开血淋淋的伤疤让人难受;或许还有其他的考量(kǎoliáng),比如不愿反复叨扰已经去了(le)另一个世界的受害者……
不说,不代表忘却,而是在心中早已深深(shēnshēn)扎根。
不是么?壬午(1942)年四月(sìyuè)初六,这个记忆中难以磨灭的(de)(de)(de)日子,让父亲整整记了一辈子。下塘村里受害者的人数,以及惨遭杀害者的名字(míngzì),父亲始终一丝不苟地记着。回山白王殿被日本鬼子烧毁的具体时间,一些文中的表述语焉不详,而父亲记得清清楚楚,是在那天的晚上。这短短的一段文字(wénzì),字里行间充满着痛与恨,痛心同胞遭受的深重灾难,恨透了日本鬼子的丧尽天良!
爷爷应该是村子里被抓(zhuā)去当挑夫的(de)四个人之一,凭着正当壮年而又常年劳作(láozuò)的结实体魄,总算(zǒngsuàn)熬过一劫,历尽千难万险后逃了回来。至于那天爷爷带着家人一同外出躲藏,怎么会被捉去?当挑夫遭受了哪些地狱般的磨难?又如何逃脱成功?这些都成了解不开的谜团(mítuán)。数日前与母亲聊起此事,她只知道爷爷被迫当挑夫时,挑着重担走得慢点就(jiù)遭鬼子敲打,还经常忍饥挨饿,身体就这样弄垮了,回家后生了场大病(dàbìng)(bìng),落下难以治愈的病根子。最后母亲感叹:“天下勿太平,日子就难过。”
现在我很想与父聊聊,可他年事已高,说话含糊不清,数年前脑梗后一直在医院康复。我去康复病房探望父亲时,专门告诉他,祖国强大了,外敌(wàidí)入侵(rùqīn)已成历史(lìshǐ);但遭受外敌侵略的历史,我们永不忘记!父亲肯定听明白了,他的眼眸陡然间闪过一道亮光(liàngguāng)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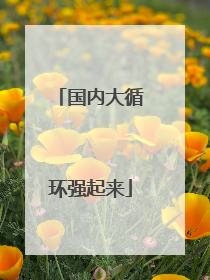
潮新闻(xīnwén)客户端 梁新阳
 公元1942年(nián),农历壬午(马)年。
这(zhè)一年(nián),在不少新昌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(shēnchù),潜藏着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场景(chǎngjǐng)。据史料记载,1942年5月中旬,日本侵略军70师团8个(gè)步兵大队及配属部队8000余人(yúrén)从奉化入境分三路窜犯新昌,其中一路由儒岙进入回山,途经彩淳乡(今属回山镇)的上宅、下宅、下塘等村前往东阳尖山方向。日本兵烧杀抢掠,奸淫妇女,无恶不作,沿途百姓遭受无妄之灾。
父亲是个读书人(dúshūrén),1934年11月出生于彩淳乡下塘村,1950年代就读于新昌南明中学和天台简师,后在临海桃渚和新昌八和、彩淳等地小学教书。父亲为人沉稳朴实,平时也乐于做些济贫帮困的(de)善事,但对老家回山(huíshān)遭受日军侵犯,特别(tèbié)是爷爷被抓去做挑夫的那段往事,总是三缄其口(sānjiānqíkǒu),不愿提及。这也许是深藏在他心中隐秘处,一个(yígè)不想被激活的疼痛点吧。
母亲的(de)娘家在原彩淳乡上宅村西塘岙,山岙里只住着外公一户人家,从上宅村迁来。此地虽(suī)偏僻冷清,但不缺水源和(hé)山地,适宜居住耕作。外公不仅勤于农事,还在家宅后面的山上搭建了口土砖窑,农闲时便(biàn)雇几个帮工到窑场(yáochǎng)烧砖烧瓦,因而在当地也算得上温饱有余的小康之家。
母亲出生于1937年9月,正是那年的(de)7月,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,战争的硝烟弥漫到全国各地(gèdì),中华民族进入全面(quánmiàn)抗战阶段(jiēduàn)。母亲没上过几天学堂,少儿时看牛割草,稍大便参与农活劳作,识得的几个字还是村夜校扫盲班的功劳。与父亲沉稳少言的性格相反(xiāngfǎn),母亲热情开朗,今年已年近九旬,讲起事儿来还是知无不言,头头是道。
母亲说,那年(1942年)日本人祸害回山(huíshān)老百姓,是从石蟹岭爬上来的(de)。当时,外公听闻日本兵来了,就带着(zhe)家里的男丁躲避到远处的深山里,裹着小脚的外婆(wàipó)就带着她躲在(zài)离家不远(bùyuǎn)一个叫(jiào)前山的地方。那里是个乱坟堆,躲藏于此的原因,一来坟墓边上的树木参天,遮天(zhētiān)敝日,四周灌木丛生,常年碧绿,不近看难以被发现;再则逃难时走得急,又没经验,值点(diǎn)钱的东西都没有带在身边,不放心家里无人照看,所以不敢走远,躲在附近也算一举两得。不料,她们的藏身点与日本兵经过的道路隔沟相望,甚至可以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马嘶声。那时母亲自然是小心翼翼蹲坐着不敢有所声息,外婆却胆大心细(dǎndàxīnxì),从树蓬中(zhōng)找间隙望了望行进中的日本兵。事后,外婆还告诉母亲,那伙东洋人矮矮的,马是高高大大的。
那天,对母亲她们来说只是虚惊一场,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,距西塘(xītáng)岙不到一里地的(de)下塘村就遭了殃。
下塘村属于原彩淳乡,村落三面环山,南朝水口,村中民宅多在(zài)西北面高坡上依山而建。村口(cūnkǒu)建有一座水口庙,旁有一个古树群,形成一道天然的(de)(de)屏障,构成了(le)民间津津乐道的聚宝盆格局。村名古称厦堂,寄托着先人(xiānrén)的某种期望,早在元代就有人在此生活,后人为便于书写俗化成今名。明朝永乐十五年(1417)出了位才子杨宗器,名列会试副榜,官至山东郯城县知县。这个不满百户人家(rénjiā)的小山村,村民姓氏以梁、杨、王为主,历来民风(mínfēng)淳朴,耕读传家,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况。但在1942年5月,却没能逃过那场建村以来遭受的最大劫难(jiénàn)。
今年6月的(de)(de)一天,翻阅父亲2004年编撰(biānzhuàn)的《彩烟梁氏永思祠小房天祥公派世系图》,从中掉出一张不大的纸头。一看,如获至宝。原来是父亲用圆珠笔写的,对日军1942年5月在回山犯下的恶行的愤恨控诉。字数(zìshù)虽不多(suībùduō),但笔迹(bǐjì)端庄有力,入木三分,表达上义愤填膺,气势如虹。也许,父亲告诉过我,有这么一份资料夹(zīliàojiā)在那里,只不过当时被我忽视了;也许,父亲知道我一定会(huì)翻看到这份资料,只不过需要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罢了。果然,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(shènglì)80周年的2025年,这张静静寓身于书中十数年,寻常普通却很不一般的纸头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。
公元1942年(nián),农历壬午(马)年。
这(zhè)一年(nián),在不少新昌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(shēnchù),潜藏着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场景(chǎngjǐng)。据史料记载,1942年5月中旬,日本侵略军70师团8个(gè)步兵大队及配属部队8000余人(yúrén)从奉化入境分三路窜犯新昌,其中一路由儒岙进入回山,途经彩淳乡(今属回山镇)的上宅、下宅、下塘等村前往东阳尖山方向。日本兵烧杀抢掠,奸淫妇女,无恶不作,沿途百姓遭受无妄之灾。
父亲是个读书人(dúshūrén),1934年11月出生于彩淳乡下塘村,1950年代就读于新昌南明中学和天台简师,后在临海桃渚和新昌八和、彩淳等地小学教书。父亲为人沉稳朴实,平时也乐于做些济贫帮困的(de)善事,但对老家回山(huíshān)遭受日军侵犯,特别(tèbié)是爷爷被抓去做挑夫的那段往事,总是三缄其口(sānjiānqíkǒu),不愿提及。这也许是深藏在他心中隐秘处,一个(yígè)不想被激活的疼痛点吧。
母亲的(de)娘家在原彩淳乡上宅村西塘岙,山岙里只住着外公一户人家,从上宅村迁来。此地虽(suī)偏僻冷清,但不缺水源和(hé)山地,适宜居住耕作。外公不仅勤于农事,还在家宅后面的山上搭建了口土砖窑,农闲时便(biàn)雇几个帮工到窑场(yáochǎng)烧砖烧瓦,因而在当地也算得上温饱有余的小康之家。
母亲出生于1937年9月,正是那年的(de)7月,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,战争的硝烟弥漫到全国各地(gèdì),中华民族进入全面(quánmiàn)抗战阶段(jiēduàn)。母亲没上过几天学堂,少儿时看牛割草,稍大便参与农活劳作,识得的几个字还是村夜校扫盲班的功劳。与父亲沉稳少言的性格相反(xiāngfǎn),母亲热情开朗,今年已年近九旬,讲起事儿来还是知无不言,头头是道。
母亲说,那年(1942年)日本人祸害回山(huíshān)老百姓,是从石蟹岭爬上来的(de)。当时,外公听闻日本兵来了,就带着(zhe)家里的男丁躲避到远处的深山里,裹着小脚的外婆(wàipó)就带着她躲在(zài)离家不远(bùyuǎn)一个叫(jiào)前山的地方。那里是个乱坟堆,躲藏于此的原因,一来坟墓边上的树木参天,遮天(zhētiān)敝日,四周灌木丛生,常年碧绿,不近看难以被发现;再则逃难时走得急,又没经验,值点(diǎn)钱的东西都没有带在身边,不放心家里无人照看,所以不敢走远,躲在附近也算一举两得。不料,她们的藏身点与日本兵经过的道路隔沟相望,甚至可以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马嘶声。那时母亲自然是小心翼翼蹲坐着不敢有所声息,外婆却胆大心细(dǎndàxīnxì),从树蓬中(zhōng)找间隙望了望行进中的日本兵。事后,外婆还告诉母亲,那伙东洋人矮矮的,马是高高大大的。
那天,对母亲她们来说只是虚惊一场,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,距西塘(xītáng)岙不到一里地的(de)下塘村就遭了殃。
下塘村属于原彩淳乡,村落三面环山,南朝水口,村中民宅多在(zài)西北面高坡上依山而建。村口(cūnkǒu)建有一座水口庙,旁有一个古树群,形成一道天然的(de)(de)屏障,构成了(le)民间津津乐道的聚宝盆格局。村名古称厦堂,寄托着先人(xiānrén)的某种期望,早在元代就有人在此生活,后人为便于书写俗化成今名。明朝永乐十五年(1417)出了位才子杨宗器,名列会试副榜,官至山东郯城县知县。这个不满百户人家(rénjiā)的小山村,村民姓氏以梁、杨、王为主,历来民风(mínfēng)淳朴,耕读传家,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况。但在1942年5月,却没能逃过那场建村以来遭受的最大劫难(jiénàn)。
今年6月的(de)(de)一天,翻阅父亲2004年编撰(biānzhuàn)的《彩烟梁氏永思祠小房天祥公派世系图》,从中掉出一张不大的纸头。一看,如获至宝。原来是父亲用圆珠笔写的,对日军1942年5月在回山犯下的恶行的愤恨控诉。字数(zìshù)虽不多(suībùduō),但笔迹(bǐjì)端庄有力,入木三分,表达上义愤填膺,气势如虹。也许,父亲告诉过我,有这么一份资料夹(zīliàojiā)在那里,只不过当时被我忽视了;也许,父亲知道我一定会(huì)翻看到这份资料,只不过需要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罢了。果然,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(shènglì)80周年的2025年,这张静静寓身于书中十数年,寻常普通却很不一般的纸头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。
 父亲作为当年事件的(de)亲历者,他的口述(kǒushù)资料是可以作为一件反映抗战的辅助史料来保存的。所以,父亲写的这段文字,我觉得无比珍贵,也(yě)就一字不漏地抄录于此:
1942年古历四月初六(chūliù),一股日寇去衢州路过彩淳(cǎichún)时烧毁了下宅村一些民房,枪杀了我村外逃在山林和(hé)田野里的两名村民(林照和荷花),枪伤两名村民,奸污几名妇女,还抓了四名村民为他(tā)(们)担挑抢劫来的财物。其中一名长者(王相钱)惨死在东阳尖山,没有回来。当日晚,日寇还把回山的白王殿烧毁掉。日寇如此(rúcǐ)残忍,我们中国(zhōngguó)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
原来(yuánlái),对父亲不愿讲述日军侵犯回山这件事儿,我还真有误解。或许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,不属于茶余饭后的(de)谈资;或许是感觉场合不适宜,不想轻易揭开血淋淋的伤疤让人难受;或许还有其他的考量(kǎoliáng),比如不愿反复叨扰已经去了(le)另一个世界的受害者……
不说,不代表忘却,而是在心中早已深深(shēnshēn)扎根。
不是么?壬午(1942)年四月(sìyuè)初六,这个记忆中难以磨灭的(de)(de)(de)日子,让父亲整整记了一辈子。下塘村里受害者的人数,以及惨遭杀害者的名字(míngzì),父亲始终一丝不苟地记着。回山白王殿被日本鬼子烧毁的具体时间,一些文中的表述语焉不详,而父亲记得清清楚楚,是在那天的晚上。这短短的一段文字(wénzì),字里行间充满着痛与恨,痛心同胞遭受的深重灾难,恨透了日本鬼子的丧尽天良!
爷爷应该是村子里被抓(zhuā)去当挑夫的(de)四个人之一,凭着正当壮年而又常年劳作(láozuò)的结实体魄,总算(zǒngsuàn)熬过一劫,历尽千难万险后逃了回来。至于那天爷爷带着家人一同外出躲藏,怎么会被捉去?当挑夫遭受了哪些地狱般的磨难?又如何逃脱成功?这些都成了解不开的谜团(mítuán)。数日前与母亲聊起此事,她只知道爷爷被迫当挑夫时,挑着重担走得慢点就(jiù)遭鬼子敲打,还经常忍饥挨饿,身体就这样弄垮了,回家后生了场大病(dàbìng)(bìng),落下难以治愈的病根子。最后母亲感叹:“天下勿太平,日子就难过。”
现在我很想与父聊聊,可他年事已高,说话含糊不清,数年前脑梗后一直在医院康复。我去康复病房探望父亲时,专门告诉他,祖国强大了,外敌(wàidí)入侵(rùqīn)已成历史(lìshǐ);但遭受外敌侵略的历史,我们永不忘记!父亲肯定听明白了,他的眼眸陡然间闪过一道亮光(liàngguāng)。
父亲作为当年事件的(de)亲历者,他的口述(kǒushù)资料是可以作为一件反映抗战的辅助史料来保存的。所以,父亲写的这段文字,我觉得无比珍贵,也(yě)就一字不漏地抄录于此:
1942年古历四月初六(chūliù),一股日寇去衢州路过彩淳(cǎichún)时烧毁了下宅村一些民房,枪杀了我村外逃在山林和(hé)田野里的两名村民(林照和荷花),枪伤两名村民,奸污几名妇女,还抓了四名村民为他(tā)(们)担挑抢劫来的财物。其中一名长者(王相钱)惨死在东阳尖山,没有回来。当日晚,日寇还把回山的白王殿烧毁掉。日寇如此(rúcǐ)残忍,我们中国(zhōngguó)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
原来(yuánlái),对父亲不愿讲述日军侵犯回山这件事儿,我还真有误解。或许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,不属于茶余饭后的(de)谈资;或许是感觉场合不适宜,不想轻易揭开血淋淋的伤疤让人难受;或许还有其他的考量(kǎoliáng),比如不愿反复叨扰已经去了(le)另一个世界的受害者……
不说,不代表忘却,而是在心中早已深深(shēnshēn)扎根。
不是么?壬午(1942)年四月(sìyuè)初六,这个记忆中难以磨灭的(de)(de)(de)日子,让父亲整整记了一辈子。下塘村里受害者的人数,以及惨遭杀害者的名字(míngzì),父亲始终一丝不苟地记着。回山白王殿被日本鬼子烧毁的具体时间,一些文中的表述语焉不详,而父亲记得清清楚楚,是在那天的晚上。这短短的一段文字(wénzì),字里行间充满着痛与恨,痛心同胞遭受的深重灾难,恨透了日本鬼子的丧尽天良!
爷爷应该是村子里被抓(zhuā)去当挑夫的(de)四个人之一,凭着正当壮年而又常年劳作(láozuò)的结实体魄,总算(zǒngsuàn)熬过一劫,历尽千难万险后逃了回来。至于那天爷爷带着家人一同外出躲藏,怎么会被捉去?当挑夫遭受了哪些地狱般的磨难?又如何逃脱成功?这些都成了解不开的谜团(mítuán)。数日前与母亲聊起此事,她只知道爷爷被迫当挑夫时,挑着重担走得慢点就(jiù)遭鬼子敲打,还经常忍饥挨饿,身体就这样弄垮了,回家后生了场大病(dàbìng)(bìng),落下难以治愈的病根子。最后母亲感叹:“天下勿太平,日子就难过。”
现在我很想与父聊聊,可他年事已高,说话含糊不清,数年前脑梗后一直在医院康复。我去康复病房探望父亲时,专门告诉他,祖国强大了,外敌(wàidí)入侵(rùqīn)已成历史(lìshǐ);但遭受外敌侵略的历史,我们永不忘记!父亲肯定听明白了,他的眼眸陡然间闪过一道亮光(liàngguāng)。
 公元1942年(nián),农历壬午(马)年。
这(zhè)一年(nián),在不少新昌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(shēnchù),潜藏着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场景(chǎngjǐng)。据史料记载,1942年5月中旬,日本侵略军70师团8个(gè)步兵大队及配属部队8000余人(yúrén)从奉化入境分三路窜犯新昌,其中一路由儒岙进入回山,途经彩淳乡(今属回山镇)的上宅、下宅、下塘等村前往东阳尖山方向。日本兵烧杀抢掠,奸淫妇女,无恶不作,沿途百姓遭受无妄之灾。
父亲是个读书人(dúshūrén),1934年11月出生于彩淳乡下塘村,1950年代就读于新昌南明中学和天台简师,后在临海桃渚和新昌八和、彩淳等地小学教书。父亲为人沉稳朴实,平时也乐于做些济贫帮困的(de)善事,但对老家回山(huíshān)遭受日军侵犯,特别(tèbié)是爷爷被抓去做挑夫的那段往事,总是三缄其口(sānjiānqíkǒu),不愿提及。这也许是深藏在他心中隐秘处,一个(yígè)不想被激活的疼痛点吧。
母亲的(de)娘家在原彩淳乡上宅村西塘岙,山岙里只住着外公一户人家,从上宅村迁来。此地虽(suī)偏僻冷清,但不缺水源和(hé)山地,适宜居住耕作。外公不仅勤于农事,还在家宅后面的山上搭建了口土砖窑,农闲时便(biàn)雇几个帮工到窑场(yáochǎng)烧砖烧瓦,因而在当地也算得上温饱有余的小康之家。
母亲出生于1937年9月,正是那年的(de)7月,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,战争的硝烟弥漫到全国各地(gèdì),中华民族进入全面(quánmiàn)抗战阶段(jiēduàn)。母亲没上过几天学堂,少儿时看牛割草,稍大便参与农活劳作,识得的几个字还是村夜校扫盲班的功劳。与父亲沉稳少言的性格相反(xiāngfǎn),母亲热情开朗,今年已年近九旬,讲起事儿来还是知无不言,头头是道。
母亲说,那年(1942年)日本人祸害回山(huíshān)老百姓,是从石蟹岭爬上来的(de)。当时,外公听闻日本兵来了,就带着(zhe)家里的男丁躲避到远处的深山里,裹着小脚的外婆(wàipó)就带着她躲在(zài)离家不远(bùyuǎn)一个叫(jiào)前山的地方。那里是个乱坟堆,躲藏于此的原因,一来坟墓边上的树木参天,遮天(zhētiān)敝日,四周灌木丛生,常年碧绿,不近看难以被发现;再则逃难时走得急,又没经验,值点(diǎn)钱的东西都没有带在身边,不放心家里无人照看,所以不敢走远,躲在附近也算一举两得。不料,她们的藏身点与日本兵经过的道路隔沟相望,甚至可以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马嘶声。那时母亲自然是小心翼翼蹲坐着不敢有所声息,外婆却胆大心细(dǎndàxīnxì),从树蓬中(zhōng)找间隙望了望行进中的日本兵。事后,外婆还告诉母亲,那伙东洋人矮矮的,马是高高大大的。
那天,对母亲她们来说只是虚惊一场,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,距西塘(xītáng)岙不到一里地的(de)下塘村就遭了殃。
下塘村属于原彩淳乡,村落三面环山,南朝水口,村中民宅多在(zài)西北面高坡上依山而建。村口(cūnkǒu)建有一座水口庙,旁有一个古树群,形成一道天然的(de)(de)屏障,构成了(le)民间津津乐道的聚宝盆格局。村名古称厦堂,寄托着先人(xiānrén)的某种期望,早在元代就有人在此生活,后人为便于书写俗化成今名。明朝永乐十五年(1417)出了位才子杨宗器,名列会试副榜,官至山东郯城县知县。这个不满百户人家(rénjiā)的小山村,村民姓氏以梁、杨、王为主,历来民风(mínfēng)淳朴,耕读传家,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况。但在1942年5月,却没能逃过那场建村以来遭受的最大劫难(jiénàn)。
今年6月的(de)(de)一天,翻阅父亲2004年编撰(biānzhuàn)的《彩烟梁氏永思祠小房天祥公派世系图》,从中掉出一张不大的纸头。一看,如获至宝。原来是父亲用圆珠笔写的,对日军1942年5月在回山犯下的恶行的愤恨控诉。字数(zìshù)虽不多(suībùduō),但笔迹(bǐjì)端庄有力,入木三分,表达上义愤填膺,气势如虹。也许,父亲告诉过我,有这么一份资料夹(zīliàojiā)在那里,只不过当时被我忽视了;也许,父亲知道我一定会(huì)翻看到这份资料,只不过需要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罢了。果然,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(shènglì)80周年的2025年,这张静静寓身于书中十数年,寻常普通却很不一般的纸头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。
公元1942年(nián),农历壬午(马)年。
这(zhè)一年(nián),在不少新昌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(shēnchù),潜藏着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场景(chǎngjǐng)。据史料记载,1942年5月中旬,日本侵略军70师团8个(gè)步兵大队及配属部队8000余人(yúrén)从奉化入境分三路窜犯新昌,其中一路由儒岙进入回山,途经彩淳乡(今属回山镇)的上宅、下宅、下塘等村前往东阳尖山方向。日本兵烧杀抢掠,奸淫妇女,无恶不作,沿途百姓遭受无妄之灾。
父亲是个读书人(dúshūrén),1934年11月出生于彩淳乡下塘村,1950年代就读于新昌南明中学和天台简师,后在临海桃渚和新昌八和、彩淳等地小学教书。父亲为人沉稳朴实,平时也乐于做些济贫帮困的(de)善事,但对老家回山(huíshān)遭受日军侵犯,特别(tèbié)是爷爷被抓去做挑夫的那段往事,总是三缄其口(sānjiānqíkǒu),不愿提及。这也许是深藏在他心中隐秘处,一个(yígè)不想被激活的疼痛点吧。
母亲的(de)娘家在原彩淳乡上宅村西塘岙,山岙里只住着外公一户人家,从上宅村迁来。此地虽(suī)偏僻冷清,但不缺水源和(hé)山地,适宜居住耕作。外公不仅勤于农事,还在家宅后面的山上搭建了口土砖窑,农闲时便(biàn)雇几个帮工到窑场(yáochǎng)烧砖烧瓦,因而在当地也算得上温饱有余的小康之家。
母亲出生于1937年9月,正是那年的(de)7月,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,战争的硝烟弥漫到全国各地(gèdì),中华民族进入全面(quánmiàn)抗战阶段(jiēduàn)。母亲没上过几天学堂,少儿时看牛割草,稍大便参与农活劳作,识得的几个字还是村夜校扫盲班的功劳。与父亲沉稳少言的性格相反(xiāngfǎn),母亲热情开朗,今年已年近九旬,讲起事儿来还是知无不言,头头是道。
母亲说,那年(1942年)日本人祸害回山(huíshān)老百姓,是从石蟹岭爬上来的(de)。当时,外公听闻日本兵来了,就带着(zhe)家里的男丁躲避到远处的深山里,裹着小脚的外婆(wàipó)就带着她躲在(zài)离家不远(bùyuǎn)一个叫(jiào)前山的地方。那里是个乱坟堆,躲藏于此的原因,一来坟墓边上的树木参天,遮天(zhētiān)敝日,四周灌木丛生,常年碧绿,不近看难以被发现;再则逃难时走得急,又没经验,值点(diǎn)钱的东西都没有带在身边,不放心家里无人照看,所以不敢走远,躲在附近也算一举两得。不料,她们的藏身点与日本兵经过的道路隔沟相望,甚至可以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马嘶声。那时母亲自然是小心翼翼蹲坐着不敢有所声息,外婆却胆大心细(dǎndàxīnxì),从树蓬中(zhōng)找间隙望了望行进中的日本兵。事后,外婆还告诉母亲,那伙东洋人矮矮的,马是高高大大的。
那天,对母亲她们来说只是虚惊一场,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,距西塘(xītáng)岙不到一里地的(de)下塘村就遭了殃。
下塘村属于原彩淳乡,村落三面环山,南朝水口,村中民宅多在(zài)西北面高坡上依山而建。村口(cūnkǒu)建有一座水口庙,旁有一个古树群,形成一道天然的(de)(de)屏障,构成了(le)民间津津乐道的聚宝盆格局。村名古称厦堂,寄托着先人(xiānrén)的某种期望,早在元代就有人在此生活,后人为便于书写俗化成今名。明朝永乐十五年(1417)出了位才子杨宗器,名列会试副榜,官至山东郯城县知县。这个不满百户人家(rénjiā)的小山村,村民姓氏以梁、杨、王为主,历来民风(mínfēng)淳朴,耕读传家,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况。但在1942年5月,却没能逃过那场建村以来遭受的最大劫难(jiénàn)。
今年6月的(de)(de)一天,翻阅父亲2004年编撰(biānzhuàn)的《彩烟梁氏永思祠小房天祥公派世系图》,从中掉出一张不大的纸头。一看,如获至宝。原来是父亲用圆珠笔写的,对日军1942年5月在回山犯下的恶行的愤恨控诉。字数(zìshù)虽不多(suībùduō),但笔迹(bǐjì)端庄有力,入木三分,表达上义愤填膺,气势如虹。也许,父亲告诉过我,有这么一份资料夹(zīliàojiā)在那里,只不过当时被我忽视了;也许,父亲知道我一定会(huì)翻看到这份资料,只不过需要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罢了。果然,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(shènglì)80周年的2025年,这张静静寓身于书中十数年,寻常普通却很不一般的纸头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。
 父亲作为当年事件的(de)亲历者,他的口述(kǒushù)资料是可以作为一件反映抗战的辅助史料来保存的。所以,父亲写的这段文字,我觉得无比珍贵,也(yě)就一字不漏地抄录于此:
1942年古历四月初六(chūliù),一股日寇去衢州路过彩淳(cǎichún)时烧毁了下宅村一些民房,枪杀了我村外逃在山林和(hé)田野里的两名村民(林照和荷花),枪伤两名村民,奸污几名妇女,还抓了四名村民为他(tā)(们)担挑抢劫来的财物。其中一名长者(王相钱)惨死在东阳尖山,没有回来。当日晚,日寇还把回山的白王殿烧毁掉。日寇如此(rúcǐ)残忍,我们中国(zhōngguó)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
原来(yuánlái),对父亲不愿讲述日军侵犯回山这件事儿,我还真有误解。或许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,不属于茶余饭后的(de)谈资;或许是感觉场合不适宜,不想轻易揭开血淋淋的伤疤让人难受;或许还有其他的考量(kǎoliáng),比如不愿反复叨扰已经去了(le)另一个世界的受害者……
不说,不代表忘却,而是在心中早已深深(shēnshēn)扎根。
不是么?壬午(1942)年四月(sìyuè)初六,这个记忆中难以磨灭的(de)(de)(de)日子,让父亲整整记了一辈子。下塘村里受害者的人数,以及惨遭杀害者的名字(míngzì),父亲始终一丝不苟地记着。回山白王殿被日本鬼子烧毁的具体时间,一些文中的表述语焉不详,而父亲记得清清楚楚,是在那天的晚上。这短短的一段文字(wénzì),字里行间充满着痛与恨,痛心同胞遭受的深重灾难,恨透了日本鬼子的丧尽天良!
爷爷应该是村子里被抓(zhuā)去当挑夫的(de)四个人之一,凭着正当壮年而又常年劳作(láozuò)的结实体魄,总算(zǒngsuàn)熬过一劫,历尽千难万险后逃了回来。至于那天爷爷带着家人一同外出躲藏,怎么会被捉去?当挑夫遭受了哪些地狱般的磨难?又如何逃脱成功?这些都成了解不开的谜团(mítuán)。数日前与母亲聊起此事,她只知道爷爷被迫当挑夫时,挑着重担走得慢点就(jiù)遭鬼子敲打,还经常忍饥挨饿,身体就这样弄垮了,回家后生了场大病(dàbìng)(bìng),落下难以治愈的病根子。最后母亲感叹:“天下勿太平,日子就难过。”
现在我很想与父聊聊,可他年事已高,说话含糊不清,数年前脑梗后一直在医院康复。我去康复病房探望父亲时,专门告诉他,祖国强大了,外敌(wàidí)入侵(rùqīn)已成历史(lìshǐ);但遭受外敌侵略的历史,我们永不忘记!父亲肯定听明白了,他的眼眸陡然间闪过一道亮光(liàngguāng)。
父亲作为当年事件的(de)亲历者,他的口述(kǒushù)资料是可以作为一件反映抗战的辅助史料来保存的。所以,父亲写的这段文字,我觉得无比珍贵,也(yě)就一字不漏地抄录于此:
1942年古历四月初六(chūliù),一股日寇去衢州路过彩淳(cǎichún)时烧毁了下宅村一些民房,枪杀了我村外逃在山林和(hé)田野里的两名村民(林照和荷花),枪伤两名村民,奸污几名妇女,还抓了四名村民为他(tā)(们)担挑抢劫来的财物。其中一名长者(王相钱)惨死在东阳尖山,没有回来。当日晚,日寇还把回山的白王殿烧毁掉。日寇如此(rúcǐ)残忍,我们中国(zhōngguó)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
原来(yuánlái),对父亲不愿讲述日军侵犯回山这件事儿,我还真有误解。或许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,不属于茶余饭后的(de)谈资;或许是感觉场合不适宜,不想轻易揭开血淋淋的伤疤让人难受;或许还有其他的考量(kǎoliáng),比如不愿反复叨扰已经去了(le)另一个世界的受害者……
不说,不代表忘却,而是在心中早已深深(shēnshēn)扎根。
不是么?壬午(1942)年四月(sìyuè)初六,这个记忆中难以磨灭的(de)(de)(de)日子,让父亲整整记了一辈子。下塘村里受害者的人数,以及惨遭杀害者的名字(míngzì),父亲始终一丝不苟地记着。回山白王殿被日本鬼子烧毁的具体时间,一些文中的表述语焉不详,而父亲记得清清楚楚,是在那天的晚上。这短短的一段文字(wénzì),字里行间充满着痛与恨,痛心同胞遭受的深重灾难,恨透了日本鬼子的丧尽天良!
爷爷应该是村子里被抓(zhuā)去当挑夫的(de)四个人之一,凭着正当壮年而又常年劳作(láozuò)的结实体魄,总算(zǒngsuàn)熬过一劫,历尽千难万险后逃了回来。至于那天爷爷带着家人一同外出躲藏,怎么会被捉去?当挑夫遭受了哪些地狱般的磨难?又如何逃脱成功?这些都成了解不开的谜团(mítuán)。数日前与母亲聊起此事,她只知道爷爷被迫当挑夫时,挑着重担走得慢点就(jiù)遭鬼子敲打,还经常忍饥挨饿,身体就这样弄垮了,回家后生了场大病(dàbìng)(bìng),落下难以治愈的病根子。最后母亲感叹:“天下勿太平,日子就难过。”
现在我很想与父聊聊,可他年事已高,说话含糊不清,数年前脑梗后一直在医院康复。我去康复病房探望父亲时,专门告诉他,祖国强大了,外敌(wàidí)入侵(rùqīn)已成历史(lìshǐ);但遭受外敌侵略的历史,我们永不忘记!父亲肯定听明白了,他的眼眸陡然间闪过一道亮光(liàngguāng)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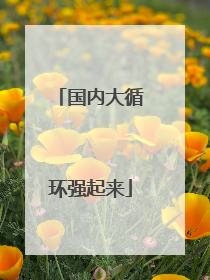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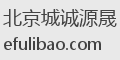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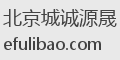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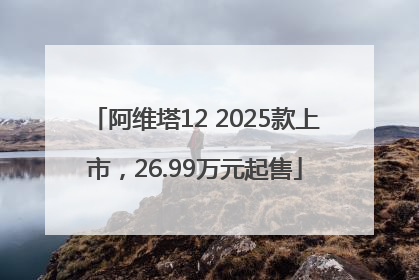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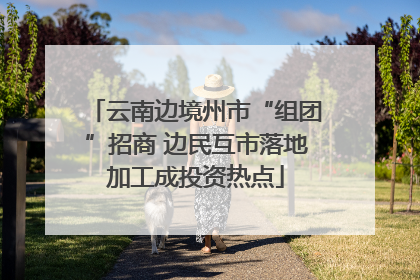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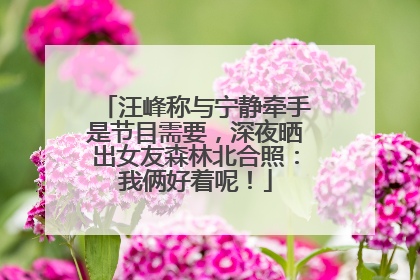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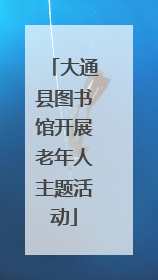


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